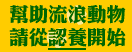--啊,這是我壞掉的房間門把,一直沒有閒錢去修它,看它跟標題頗合,所以......(茶)
------------
作者:張耀升
出版社:木馬文化
出版日期:2003年11月
------------
假若「傷痛」與「死亡」是成長所需之必經,那麼透過成長,人會變得更加身心成熟,亦或是持續不斷的墜落?《縫》一書中,集結了七篇短篇,篇幅之間看似無關,卻是連承一氣的成長歷程,是一體完整的灰澀青春成長史。
首篇故事〈縫〉,講述西服店裡,家人間的人際疏離,父親與祖母之間的非善而怨,祖母與孩童時期的主人公的祖孫親暱感情。父親與祖母間的迥異又相似的偏執,終讓彼此走向現實之外的黑洞。
敘事以第一人稱出發,讓主人公回想幼時家中事項,娓訴雙親將朽老的祖母視為不必要之存在,將其禁錮在灰暗的閣樓裡與世隔絕,而主人公用衣架頂開天花板,便能出現一道自由進出閣樓的縫隙,以維繫他與祖母的時光。就中國重孝的觀念來說,父親將祖母軟禁在閣樓就是非常不孝的事,然而他們卻將此視為家中的一種平靜手法,有違倫常,顯現出此篇的「縫」,不只是西服店原有的「裁縫」,也是主人公與祖母連繫的「縫隙」,更是家人之間情感的「裂縫」。
祖母逝世後,父親表面佯裝失母傷痛,實則施行更駭人的行為,將祖母的遺身與體面的西服縫在一起,再次挑戰中國盡孝的觀點,書中並未點出主人公的父親為何與祖母行同陌路,只點說父親將祖母的每一句話視為針刺,無論是多家常的一句話,都像是一種詛咒,像父親與祖母連承的兩代詛咒,為彼此的身軀做最殘身的肉裁,所以父親最後也像發了瘋似的將自己放逐到閣樓,重蹈祖母所歷。看似瘋狂,轉想到現今諸多新聞事件,也不乏一言不合,就持刀殺害父母親等事件,整個社會的倫常正受到一種扭曲變形的挑戰,再回頭看〈縫〉裡互仇的母子,似乎也不特別奇怪。
假若覺得礙眼的人,流放至閣樓,眼不見為淨就好了,多奇怪的家庭觀念,家人之間該是最能彼此羈絆掛懷的,在匆忙而速食的現今社會,連家人之間的感情都能比陌生人疏離,明明同住一個書簷下,卻有隱形的鴻溝將彼此間隔,但我以為,父親是有想嘗試去做修補的動作,他想改變家人間的疏離,僅管他選擇的方式是趁主人公睡眠時,拿著針線縫補主人公因他受傷的手,他是如此的認真。
我被強烈的刺痛感驚醒,只見父親蹲在我床邊,左手撫摸我手上的疤痕,右手拿著針線,他說:「乖,這兩片肉沒縫好,縫線外露很難看,我幫你弄個無縫針織。」(P.22)
在人體上直接針縫,視他發瘋也不為過,但父親究底是藏了一片心意,被警察押走前,他大聲嚷著:「一定會縫得不留痕跡的。」不曉得這是對主人公,還是對他自己心靈喊話。家人間的縫隙之大難以估量,僅管他想將其「縫得不留痕跡」,卻無力回天了,長久的疏離已經讓他無法仔細思考其他方法,他只將一切失敗歸究在死去的母親身上。愈縫愈大的洞,讓全家都陷入偏離的相處軌道,在失控的邊緣上遊走,平衡的支點,終還是建立在「忽視」上,父親忽視祖母,主人公試著忽視父親,彷若成了一種微妙的表面家庭和諧的定則,縫補不起來的關係縫隙,就只能眼睜睜的看它淪闊為黑洞,可懼,也讓人省思親人家那份微妙又陌生的情誼,除卻血緣,還有什麼是能讓彼此緊緊聯繫的?如果沒有試著做出努力,也許也會像書中家庭,淪為一種代代相承的詛咒了。
第二篇〈螳螂〉,則是敘述甫踏進職場的新鮮人,痛失祖母而感到徬徨無助,他選擇以將祖母遷出靈骨塔,將其落地入土為夢想,然工作職場像是騙局與謊言的包裝體,待他察覺,他已經是靈骨塔的推銷員,他孤注一職,卻感覺將祖母出賣,自己仍然渺小如天地間一隻小蟲。
接續了前篇〈縫〉中,主人公與祖母彼此相偎的親密,所以在祖母去世後,彷若是悲劇性的全面降臨,人生避風港的頓隱,排除了第一人稱,〈螳螂〉選擇第三人稱的全知觀點,像是從過去的自我回憶中抽拉回現實,是不能自己一手掌握的世界,所以主人公對他即將面臨的職場生活如此提到:
讓冰冷的自來水刷掉整夜無益的多想,深色襪子、西裝褲、白襯衫、領帶、西裝外套,這一切像是堅硬的裝甲,戴上他們後他便得投身外面的世界,像個戰士殺出一條血路。(P.30)
他是如此的無助,只能透過嚴謹的外表讓自己假裝堅強,好面對未知的世界,雖滿心惶懼,但一想起那微小的夢想,他便硬著頭皮為自己殺出一條血路。然而在他說了違心之論成功推銷了靈骨塔位後,他迷惘了,他以祖母當一個商品實證向社會大眾推銷,他是不是出賣了自己也出賣了祖母?他想起,自己也該走出自己的路,沒有了可以休息依靠的港灣,他仍需要勇敢的走下去,他告誡自己,別再忘記祖母已離世的事實。像是郝譽翔《那年夏年,最寧靜的海》裡提到的,「死者逮住生者,而生者從此被判終生監禁」般,男子無助,所能想起的美好記憶都是祖母給予的,然祖母已不在人間,點點滴滴的生活片段讓男子無法跳脫,儘管他捧著花束來向祖母做最後的道別,仍無法將思緒理個斷明,他想起祖母出殯那時,曾有螳螂飛到擋風玻璃前,父親對他說,那是祖母捨不得他,回來見他。我以為,螳螂的存在著實重要,為什麼不是別的昆蟲,偏得是螳螂不可?恐怕是引用了「螳臂擋車」的典故吧,故事中的男子,想著公司主任說的,「人,不過是一隻小蟲啊!」,像一隻蟲要面對龐然巨大的社會,不也是意味職場新鮮人的「螳臂擋車」嗎?化成螳螂,也就能當做祖母從未離去,自己仍然有人可以依靠,自我催眠般的無奈,就算是小蟲,就算是擋車,還是得生存下去,無論一路上拋丟了什麼過往自己最看重的存在,主人公難過,但也是認清了職場生存所必須面對的殘酷,給自己設了限,等同斷了自己的路。諸多的抱歉,都只能化為一束花,化在漆黑的夜裡了。
第三篇〈敲門〉,是描寫服兵役的軍官休假的一天。男子為求假期飽受輔導長屈辱,出了軍營,他尋找一切他想抒壓的音樂與書籍卻一再受挫,他決定放棄,改打公共電話給女友,女友未接,改打給人在醫院的祖母,斷斷訊訊的公共訊號探出不安的訊息,他想去探望祖母,又再次受挫,只能冷著心,失意而傷憤的回到軍營。
同樣延續前兩篇的情緒,〈敲門〉似乎是主人公在遭遇家庭的不和諧,與微小的夢想受挫後,試著向外協詢,他詢求他想要的一切可能,且一路所遇皆是冷默的面孔,如在他謙卑的對向他示好的軍營門口衛兵說不用緊張,他只是一個佔著下士缺額的小兵,衛兵卻暗自以此嘲笑他;計程車司機胡亂的漲價,坑他的錢;在唱片行裡,想尋找貝多芬及布拉姆斯的音樂,櫃檯小姐無視他的詢問,他轉而尋向書店,想找喬艾斯的《尤里西斯》未果,福克斯的《聲音與憤怒》也無下文,書店店員投以尖銳的目光。一路所遇皆非良善,一日的休愜成了一日的負面堆疊,直到他打電話給祖母,所有的負面凝聚成莫大的恐慌,路旁馳過的救護車聲更篤定了他的不祥預感。
喔咿第一聲是提醒,喔咿第二聲是催促,喔咿第三聲是警告,喔咿第四聲是重擊!(P.68)
一日所遇在此化做一個恐懼炸彈。他的希望是如此微渺,只是想回到台中探視祖母一面,好安切自己的心,然而連如此渺小的願望都破碎,飛機的後補機位輪不到他。
他試著透過一天的對外假期,小心探求一些安穩的因子,沒有多餘的奢想,小心翼翼,求援般地走出戶外,可憐如他,頓時整個世界都與他為敵,他只能焦慮,以及默默承受這一切難堪與冷默的對待。人際疏離的範圍,由此從家庭闊大到整個社會了。每個人對自己以外的周遭事物都顯得陌不關心,層層築起的高牆,訴說著防備與冷漠。總還是天真的認為,世上還是有溫情存在,所謂冷暖人間,有「冷默」也一定會有「溫暖」,但主角的心境本身就偏向有些灰暗,像是伸出了雙手,卻不敢大聲喊道請扶我一把的失意者,安安靜靜的向隅,什麼樣的心境會看到什麼樣的周遭,也許仍有好的事情發生,但在那個當下,已經焦慮到一個臨界點的主角,恐怕只能留意到帶著惡意的冷箭了,他以為他找不到能夠幫助他的回應,每個人給予他的就只有冷默。主角想要全世界之中的一些暖溫,然冷默將他推向了世界的邊緣,候時滅隕。
無論是誰,失意時都希望有人能拉自己一把,或給自己一個微笑,無論是多微小的動作,都能像太陽似的給予溫暖,但試問,如果別人不給予,難道自己就給不起自己一點繼續下去的力量嗎?自己不能當自己一天的太陽嗎?哪怕是一天也好,盲昧期待別人伸援,等同將自己的一切交由別人掌控了。每個人,一定有只屬於自己珍貴的一部分,是別人拿不起也搶不走的,抱持一點陽光心態,也許所遇仍然糟糕,但心境上或許就不會像〈敲門〉一篇,被外界的聲音所影響後情緒紛亂,只知道自己陷入了憤怒的情緒,卻又讓此情緒自殘般焚燒自己了。
第四篇〈暘城〉,講述單親家庭的國小生,面對母親將生活壓力改成對他的誤解、姊姊遠在家鄉,朋友也因家庭背景的衰微排擠他,他書寫家庭完美的假象催眠自己,然累積滿腹的淚水終於無法負荷,而適巧回家的姊姊,給予他微渺希望以期冀未來。
〈暘城〉其實是令人非常難過的一篇。小小的孩子,在面對父親驟逝家庭巨變後,沒有家庭的溫暖給予慰藉了,時逢國小階段,是小孩子初建立友誼與學習人際關係的階段,曾經歃血為盟的朋友,卻相繼背叛了他,一瞬間全部都破裂了,還懞懂無知的小孩,哪裡知曉自己為何會受到這樣的對待。
鄰居長長呼了一口氣,轉過頭不看他說:「你們家很窮啦!我媽說會被帶衰。」
厚重的鐵門關上時發出響亮的一聲卡喳,他只來著及問:「我們不是......」後半句「結拜兄弟嗎?」哽在喉嚨,他說不出來。(P.90)
除此之外,年紀稍長的朋友在面對成長的迷惘時,選擇以強權欺侮來證解,多可怕的惡性循環。拳頭的強勢,其實無法真的得到人心的愛戴,擁有的只有表面稱兄道弟,如果人與人之間的情誼非得以層階建立,對小孩來說,未免是太早接觸的社會現實了。
他們的友情在國中生畢業後就消失了。國中生藉由欺負他來證明自己已經邁入另一個階段,證明自己不再弱小,隔壁巷子裡每個男孩子都是這麼過來的,他不知道這是誰開啟的傳統,現在輪到他來忍受這充滿屈辱的磨練,而改天,過了幾年後,他就會擁有欺負別人的特權。(P.79)
看來有些誇張的情節,其實也只是社會現象的一隅,家長的輿論對成長階段的孩童本身就極具影響力,現在許多社會新聞在播報重大罪行的犯罪者,當畫面播到小孩子時,總是巧妙的打上馬賽克,怕小孩子無論在校園及生活中生存,人們的指指點點,是最殘忍的重傷害。僅管本文中的小孩所遇是父親逝去,家中的債務難以清還,並非任何犯罪行為,但因為有討債公司上門,街坊鄰居就會告誡小孩,誰家誰家的小孩千萬不要靠近,以往被歸類到習以為常的事情,當真的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時候,恐怕只能把無奈與心酸往心裡吞了。
因為採用第一人稱,透過小孩子的視野感受著他每一寸的讓步與每一步努力後的退縮,著實令人心疼。當小孩唸著自己登上國語日報的作品〈甜蜜的家園〉,他自己塑造一個美好的家庭生活,好山好水,家人間互相友愛,是個溫暖而無煩憂的好所在。他一次又一次的唸著,像是要刻盡自己腦袋的唸著。怎麼會淪到這種地步呢?怎麼會讓小孩,無助到要自己創造一個假象,好讓自己有動力持續向前。當假象被道破,赤裸裸的現實襲來,過大的反差,只會更感難受,最後,他試著向外地的姊姊求救了,他再也無法用謊言欺瞞自己一切仍然美好了。姊姊說著一切都會好轉,長大就沒事了,然而,承載所有傷痛的心靈,已無法安穩的長成一個健全的個體,也許現在的一切都會好轉,但未來又會遇到什麼困境呢?沒有人知曉,他也管不著,他連自己的今天過不過得去都不知道,光亮的明天真的會到來嗎?沒有人能肯定,只知道,他自己仍必須走下去。
第五篇〈藍色項圈〉,是在一間象徵權勢財力的私立中學裡,學生們在高壓下激烈競爭,在老師極端不平衡的對待下,學生們一個個在鬧鬼的宿舍寢室裡透過死亡換取新生,貧寒出身的主人公傾盡全力仍無法獲得好的表現,在友人死去的打擊下,他選擇進入鬧鬼的寢室,將自己成為殘酷體制下一員。
只要曾經當過學生,且遇到以成績斷定學校好壞的班級導師,對這一篇肯定是感觸很深。雖是採用第一人稱的我,但主人公從頭至尾都未曾出現其姓名,只是安安靜靜地娓訴他的校園生活,生活的貧困讓他在所謂的貴族學校裡非常不自在,因此他選擇低調,然低調與低落的成績,讓他在校園幾乎抬不起頭來。這裡的老師並沒有扮演傳教、授業、解惑也的角色,他傳達的只有「成績至上」,除了成績,一切都是多餘的,甚至是要求成績好的學生離間成績差的學生,將成績不好的學生視為感染性強烈的病毒,也許是現在教育的方針,使人感覺這部分有些誇張了,許是想要更突出學生在升學體制下的彷徨,加上不能給予救援的老師,使著國中生的主角在此篇中更顯卑微無助了。
乍看篇題〈藍色項圈〉,還懷抱著一種浪漫情懷,當發現這是一種透過上吊死亡卻離奇重生的印記,反倒顯得駭然了。主人公曾經覺得自己特別,因為自己曾在母親的娘胎裡死過一次卻奇蹟似的生還,到了這間學校,他發現他錯了,他在這裡一點也不特別,這裡許許多多的資優生或高材生都死過,而且死過好幾次,那脖頸上的藍色勒痕像是蛇一般的纏成一圈,他們稱之為藍色項圈。我假想,為什麼要求全體都必須住宿的學生宿舍,會有這麼一間全校皆知鬧鬼的寢室,許是多年來許多受體制壓迫下的學生,一個個選擇在此上吊身亡,直到怨氣與執念集合到一個臨界點,便有了神奇的力量。
那間寢室會讓死者再活過來,他們會帶著脖子上的淤青,從衣櫃裡爬回現實世界,然後成績突飛猛進,因為他們已不是人類。(P.115)
以一種鬼魅的方式書寫,也意味著學校對這裡的學子而言,已非學習的殿堂,而是充滿明爭暗鬥,只能在自毀或毀人中做選擇。書中主人公看著學校想著「那是監獄,一棟有著六層樓高圍牆,就算插翅也難飛的監獄。(P.120)」,在許多專家在討論學生們的教改問題時,真的是為學生設想嗎?曾利用大三升大四的暑假,到南投嘉和國小帶一群準備升小二至小六的小學生,當他們的暑期輔導老師,看著他們的暑假作業本,我很訝異,小五的數學題目出現國中才會教的一元二次方程式,題目卻又規定不能設x、y值,因為是數間學校的小朋友集合在一間國小共同上課,大同小異的作業本讓我看到無言,這怎麼會是出給小學生的題目?該是學習基礎的階段,卻一直拋丟越級的知識,怎麼會有辦法消化?簡直要把小學生訓練成萬能妖怪一樣,小孩子的快樂童年呢?我感到疑惑。口頭說著對學生著想,實際上職管教育的人,對國小生的題目自己也不一定答得出來,諷刺極了。對照書中的主角,他便是處在一間要求更嚴謹暴慄的地方,標準是一百分,少一分打一下,當每週假日回家,家人詢問學校生活如何時,可能原想哭訴的,卻因為父親的期待而將所有苦楚吞回自己的肚子,難以消化。
「要用功一點喔!我們可是到處借錢才有辦法勉強讓你進去那裡讀的。」
「嗯,我知道。」
「我們沒有什麼能留給你的,要好好讀書,不要像你老爸一樣,沒有學歷也沒有專長,一輩子讓人瞧不起。」(P.118 -119)
我想,大多同我一樣貧苦家庭中長大的小孩,聽到雙親對自己說這樣的話時,就算在學校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也只會跟書中主人公做同樣的回應吧。所以主人公這麼想的。
幾乎都是這樣的對話,讓我無法告訴他們那個學校的課業壓力早就遠遠超過一個十二歲小男生所能承受的極限,為了生存我們可是幾乎什麼事都幹得出來啊!
挨打到麻痺的掌心,包著深藍色書套咀嚼不爛無法下嚥的課本,裏著深藍色制服的虛弱身體,還有貼著黑眼圈的沉默的臉,而身體與臉的交接處印著一條深藍色的項圈。我的青春期塞滿深藍色的空白。(P.119)
已經不是單純的學習壓力了,如果說學校就是一個小社會,那麼他所面對的,毫無疑問的就是生存壓力,標榜適者生存,不適者亡,殘酷極了!諸多的壓力加上室友阿文的死亡,他終於放棄堅持自己的正道,他選擇了將脖頸套上鬧鬼寢室麻繩,他要成為體制的一員,一起淪落。誰都沒有資格責怪他選擇走上這條路,這是整個教育體系的問題,他只是冰山一角的犧牲品,因為他只是冰山一角,就更令人難過了。國中,本該是充滿叛逆又充滿年少輕狂的年紀,然他的青春期塞滿了深藍色的空白,深藍色,不只是學校制服的顏色,頸項勒痕的顏色,也是他心中滿據的憂鬱,找不到出口的眼淚,凝聚成他悲傷的個體。學習成長,用生命作為代價未免太苛刻,假若連生命都必須要出賣才得以生存,我們的教育真的需要省思,而非將學生當做白老鼠一樣的做實驗,當做在壓模雞蛋糕似的壓出一模一樣性格的學生,覺得失敗就再做一次教改,又是一次全新的實驗,可憐的不是大人,而是在這樣混亂體制下成長的學生。
第六篇〈友達〉,可以說是〈藍色項圈〉的續集,延續著〈藍色項圈〉的發展,為其中阿文的死做解答。警方開始調查阿文的死因,老師直接懷疑成績並非頂端,又曾經是阿文室友,即〈藍色項圈〉的主人公,同樣是以升學壓力為題,不同的是,改以小強做為敘述主體,小強的本名是林友達,「友達」在日文為朋友之意,但他的成績總是吊車尾,所以也是被老師要求學生們排擠的對象,沒有朋友就像是一種諷刺,然他卻像打不死的蟑螂,一路攀升直到優等生的地位,中途也是受到鬧鬼寢室的上吊洗禮,但他非常孤獨,他總想早一步跨入成人的社會,脫離監獄般的學校。他景仰阿文的室友,阿文的室友卻誤以為阿文是他害死的,他原先以為全校除了阿文,也許就只有阿文的室友可以理解他,然一切都是他的假想,他以為,他的世界破碎了,再也沒有什麼值得信任。所以他將所有的情緒封包在一紙信條上,收拾自己的破碎。
紙條懷著小強的訊息在空中一圈圈地翻滾,上面寫著「進入成人世界後,就算被羞辱被暗算,也只能笑給別人看。對方也許臉上帶著微笑,卻可能早就和自己結下了樑子,以為對方是朋友,每次相處都加深對方對我的怨恨,而我,什麼都不知道。」(P.152)
看似強勢的小強,其實跟學校裡的每個人一樣脆弱,甚至他的遭遇跟阿文的室友很相似,都是揹著家人強烈的期望進入學費貴得嚇人的學校,也曾遭排擠,也曾是朋友,其實很雷同的。如果沒有阿文事件的陰影,模糊的畫線在兩人之間,或許能成為莫逆之交也未可知,然誤解在兩人心中紮根,已無其他可能。他做了選擇,他要將一切責究推給阿文的室友,他陷害了阿文的室友。
這是小強懦弱又強勢的反應,因為脆弱所以堅強,因為害怕所以強勢,都只是一種偽裝。誠如〈螳螂〉一篇說的,「人啊,不過是一隻小蟲!」小強不擇手段,讓自己回到班上的核心人物,什麼人情義理全部都拋開了,一切都是假象,他包裝自己的情感,成為體制下的核心,無論精神已被掘空,只剩一具外殼。明明是強勢的踩著別人的背往上爬,卻彷彿能聽到小強泣血般的控訴,是整個局勢讓他不得不如此,一腳踏進了成人世界,也等同捨棄了所有的天真與青春。所以書末說他一腳踏進了成人世界,也等同將自己推向另一處魔境,肉弱強食的現實世界,年輕的身軀裝著如此衰老的心靈,教人怎能不扼腕?
終篇〈伊卡勒斯〉,講述已婚男子矛盾而迷離回憶過去室友忠哥對他的情感包懷,因為他的任性與無以察覺,將忠哥推向了死亡之森的樹海,十年後,搭乘飛機回台灣的過程,他遇見和忠哥極相似的赤松森作,他更改行程的跟隨赤松森作到日本,然他理解他已非過去的自己,忠哥也不復存在了,無法事過境遷,於是他同樣乘著飛機回到台灣,在忠哥給予的回憶中反覆傷害自己。
〈伊卡勒斯〉以過去跟現實雙線並行,過去的自己恣意忽視忠哥的付出,就算是想回以溫暖的語句,說出口的卻總是傷人,忠哥看似默默的承擔,心中卻藏著一把野火,將自己一點一滴的燃噬,並以南方之星的〈真夏的果實〉貫穿全場,歌詞明白的表示:
「正如負一百度的太陽,談一場不會帶來溫暖的戀愛。令人眩目的真夏的果實,至今仍綻放心底。」
原來是一場絕望的戀愛。(P.163 - 164)
年輕時戀愛的界限模糊不明,透過一曲絕望的歌曲,暗渡了忠哥的心情,儘管多年後,主角了解也深受憾動,卻也改變不了天人永隔的距離,如此相近,又難以靠近了。
十年前忠哥走進樹海,現在的我躺在赤松森作身旁。時間與空間現在都是模糊的線條,可以任意扭曲或折疊,我背負著十年的寂寞往回走到原點,而忠哥卻在十年前就停下來等我,一直等到我能愛他為止。(P.183)
同志之情被視為違反常理,所以作者選擇用死亡的距離讓他們彼此貼近,一把野火將彼此焚燒,差別在於,前者忠哥走近樹海,後者的自己則被忠哥判了終生監禁,獨嚐往後一個人的孤寂,然他不能再想了,他有妻兒等他回去,他已經不是像年輕時可以對忠哥耍任性的自的,忠哥曾受愛火燒疼的苦,他用回憶反噬。再不能回去了。同性戀在台灣已起步,近年來諸多的活動舉辦,如同志彩虹遊行,在台灣已經成為同志每年的例行活動,他們是少數的一群,但並非病態,也非活該受歧視。總有一天,他們也能走向自己的路,而非像〈伊卡勒斯〉裡的三個男人,徘徊在社會的邊緣,猶豫要不要跨過最後一道性別的防線,還是受制於現實社會的倫常壓力。
再者,〈伊卡勒斯〉放在最後一篇,也有統整七篇之意,神話中的伊卡勒斯與父親用蠟造了一對翅膀一同飛離宮殿,然伊卡勒斯忘卻父親的警告,愈飛愈高,直至蠟融的翅膀,伊卡勒斯從高空中狠狠摔落。
每一篇的人物都在面對生命成長各時期的困頓,張耀升在介紹《縫》的時候做了如此解釋:
五年級的《伊卡勒斯》、《縫》,六年級的《螳螂》、《敲門》,七年級的《藍色項圈》、《友達》、八年級的《暘城》,是這個世界上五年級以下的所有人同時承受的創痛,也是他們曾經、目前、或將來得面對的難題。
每個人都耗盡心力的面對挫折,往自己心中美好的夢想前進,同時也因為追逐夢想而燒融了羽翼,〈伊卡勒斯〉裡強調「飛機起飛還是為了降落」,以此為每個人的墜落下了注解,明明都是如此的拚命,為微小卻重要的夢想而努力,卻總在起飛與降落中飄盪不定,就算克服了現下的困難,未來仍然得面對數不清的難題,愈是努力,愈是容易產生裂縫,就如同伊卡勒斯,飛的愈高,高到靠近了天,代價是愈深的陷落。萬劫不復的像是詛咒。
綜觀此書,張耀升沒有選擇帶有希望結尾的方式,呈現了成長時期的黑暗面,投射一團又一團的負面訊息,集結成一個偌大的黑洞,教人震懾書中篇幅的同時,也受到巨大的陰暗氣息影響,換個方向來看,也帶著一種期許,狄更斯《雙城記》在卷頭便寫道: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面前有著各樣事物,人們面前一無所有;我們全都會上天堂,也全都會下地獄。
當所有負面凝聚到一個臨界面,全新的力量也將誕生,許是中國人說的否極泰來了,正因為有黑暗的經歷,才更能體會與珍惜感受光明與希望的瞬間。且成長,是一條不能回頭的路,只能選擇繼續前進,或原地踏步後被時間催著年華老去,就算努力所換來的是持續不斷的墜落,也是一種成長,一路上所有的苦痛辛酸,也許年老時回想,一切苦難都已是微風吹拂而過一片落葉,輕描淡寫了。
---------。。
後記:
破了自己寫心得的字數紀錄啦!果然,有老師逼著分析小說做報告就是不一樣啊!
但......唔,正常的小說心得,是不能這樣把內容爆光光吧,但這是小說賞析兼心得報告,所以,啊哈哈......因為小說老師大好人的給了很好看的報告分數,所以很高興的放上來啦
--啊,這是我壞掉的房間門把,一直沒有閒錢去修它,看它跟標題頗合,所以......(茶)
------------
作者:張耀升
出版社:木馬文化
出版日期:2003年11月
------------
假若「傷痛」與「死亡」是成長所需之必經,那麼透過成長,人會變得更加身心成熟,亦或是持續不斷的墜落?《縫》一書中,集結了七篇短篇,篇幅之間看似無關,卻是連承一氣的成長歷程,是一體完整的灰澀青春成長史。
首篇故事〈縫〉,講述西服店裡,家人間的人際疏離,父親與祖母之間的非善而怨,祖母與孩童時期的主人公的祖孫親暱感情。父親與祖母間的迥異又相似的偏執,終讓彼此走向現實之外的黑洞。
敘事以第一人稱出發,讓主人公回想幼時家中事項,娓訴雙親將朽老的祖母視為不必要之存在,將其禁錮在灰暗的閣樓裡與世隔絕,而主人公用衣架頂開天花板,便能出現一道自由進出閣樓的縫隙,以維繫他與祖母的時光。就中國重孝的觀念來說,父親將祖母軟禁在閣樓就是非常不孝的事,然而他們卻將此視為家中的一種平靜手法,有違倫常,顯現出此篇的「縫」,不只是西服店原有的「裁縫」,也是主人公與祖母連繫的「縫隙」,更是家人之間情感的「裂縫」。
祖母逝世後,父親表面佯裝失母傷痛,實則施行更駭人的行為,將祖母的遺身與體面的西服縫在一起,再次挑戰中國盡孝的觀點,書中並未點出主人公的父親為何與祖母行同陌路,只點說父親將祖母的每一句話視為針刺,無論是多家常的一句話,都像是一種詛咒,像父親與祖母連承的兩代詛咒,為彼此的身軀做最殘身的肉裁,所以父親最後也像發了瘋似的將自己放逐到閣樓,重蹈祖母所歷。看似瘋狂,轉想到現今諸多新聞事件,也不乏一言不合,就持刀殺害父母親等事件,整個社會的倫常正受到一種扭曲變形的挑戰,再回頭看〈縫〉裡互仇的母子,似乎也不特別奇怪。
假若覺得礙眼的人,流放至閣樓,眼不見為淨就好了,多奇怪的家庭觀念,家人之間該是最能彼此羈絆掛懷的,在匆忙而速食的現今社會,連家人之間的感情都能比陌生人疏離,明明同住一個書簷下,卻有隱形的鴻溝將彼此間隔,但我以為,父親是有想嘗試去做修補的動作,他想改變家人間的疏離,僅管他選擇的方式是趁主人公睡眠時,拿著針線縫補主人公因他受傷的手,他是如此的認真。
我被強烈的刺痛感驚醒,只見父親蹲在我床邊,左手撫摸我手上的疤痕,右手拿著針線,他說:「乖,這兩片肉沒縫好,縫線外露很難看,我幫你弄個無縫針織。」(P.22)
在人體上直接針縫,視他發瘋也不為過,但父親究底是藏了一片心意,被警察押走前,他大聲嚷著:「一定會縫得不留痕跡的。」不曉得這是對主人公,還是對他自己心靈喊話。家人間的縫隙之大難以估量,僅管他想將其「縫得不留痕跡」,卻無力回天了,長久的疏離已經讓他無法仔細思考其他方法,他只將一切失敗歸究在死去的母親身上。愈縫愈大的洞,讓全家都陷入偏離的相處軌道,在失控的邊緣上遊走,平衡的支點,終還是建立在「忽視」上,父親忽視祖母,主人公試著忽視父親,彷若成了一種微妙的表面家庭和諧的定則,縫補不起來的關係縫隙,就只能眼睜睜的看它淪闊為黑洞,可懼,也讓人省思親人家那份微妙又陌生的情誼,除卻血緣,還有什麼是能讓彼此緊緊聯繫的?如果沒有試著做出努力,也許也會像書中家庭,淪為一種代代相承的詛咒了。
第二篇〈螳螂〉,則是敘述甫踏進職場的新鮮人,痛失祖母而感到徬徨無助,他選擇以將祖母遷出靈骨塔,將其落地入土為夢想,然工作職場像是騙局與謊言的包裝體,待他察覺,他已經是靈骨塔的推銷員,他孤注一職,卻感覺將祖母出賣,自己仍然渺小如天地間一隻小蟲。
接續了前篇〈縫〉中,主人公與祖母彼此相偎的親密,所以在祖母去世後,彷若是悲劇性的全面降臨,人生避風港的頓隱,排除了第一人稱,〈螳螂〉選擇第三人稱的全知觀點,像是從過去的自我回憶中抽拉回現實,是不能自己一手掌握的世界,所以主人公對他即將面臨的職場生活如此提到:
讓冰冷的自來水刷掉整夜無益的多想,深色襪子、西裝褲、白襯衫、領帶、西裝外套,這一切像是堅硬的裝甲,戴上他們後他便得投身外面的世界,像個戰士殺出一條血路。(P.30)
他是如此的無助,只能透過嚴謹的外表讓自己假裝堅強,好面對未知的世界,雖滿心惶懼,但一想起那微小的夢想,他便硬著頭皮為自己殺出一條血路。然而在他說了違心之論成功推銷了靈骨塔位後,他迷惘了,他以祖母當一個商品實證向社會大眾推銷,他是不是出賣了自己也出賣了祖母?他想起,自己也該走出自己的路,沒有了可以休息依靠的港灣,他仍需要勇敢的走下去,他告誡自己,別再忘記祖母已離世的事實。像是郝譽翔《那年夏年,最寧靜的海》裡提到的,「死者逮住生者,而生者從此被判終生監禁」般,男子無助,所能想起的美好記憶都是祖母給予的,然祖母已不在人間,點點滴滴的生活片段讓男子無法跳脫,儘管他捧著花束來向祖母做最後的道別,仍無法將思緒理個斷明,他想起祖母出殯那時,曾有螳螂飛到擋風玻璃前,父親對他說,那是祖母捨不得他,回來見他。我以為,螳螂的存在著實重要,為什麼不是別的昆蟲,偏得是螳螂不可?恐怕是引用了「螳臂擋車」的典故吧,故事中的男子,想著公司主任說的,「人,不過是一隻小蟲啊!」,像一隻蟲要面對龐然巨大的社會,不也是意味職場新鮮人的「螳臂擋車」嗎?化成螳螂,也就能當做祖母從未離去,自己仍然有人可以依靠,自我催眠般的無奈,就算是小蟲,就算是擋車,還是得生存下去,無論一路上拋丟了什麼過往自己最看重的存在,主人公難過,但也是認清了職場生存所必須面對的殘酷,給自己設了限,等同斷了自己的路。諸多的抱歉,都只能化為一束花,化在漆黑的夜裡了。
第三篇〈敲門〉,是描寫服兵役的軍官休假的一天。男子為求假期飽受輔導長屈辱,出了軍營,他尋找一切他想抒壓的音樂與書籍卻一再受挫,他決定放棄,改打公共電話給女友,女友未接,改打給人在醫院的祖母,斷斷訊訊的公共訊號探出不安的訊息,他想去探望祖母,又再次受挫,只能冷著心,失意而傷憤的回到軍營。
同樣延續前兩篇的情緒,〈敲門〉似乎是主人公在遭遇家庭的不和諧,與微小的夢想受挫後,試著向外協詢,他詢求他想要的一切可能,且一路所遇皆是冷默的面孔,如在他謙卑的對向他示好的軍營門口衛兵說不用緊張,他只是一個佔著下士缺額的小兵,衛兵卻暗自以此嘲笑他;計程車司機胡亂的漲價,坑他的錢;在唱片行裡,想尋找貝多芬及布拉姆斯的音樂,櫃檯小姐無視他的詢問,他轉而尋向書店,想找喬艾斯的《尤里西斯》未果,福克斯的《聲音與憤怒》也無下文,書店店員投以尖銳的目光。一路所遇皆非良善,一日的休愜成了一日的負面堆疊,直到他打電話給祖母,所有的負面凝聚成莫大的恐慌,路旁馳過的救護車聲更篤定了他的不祥預感。
喔咿第一聲是提醒,喔咿第二聲是催促,喔咿第三聲是警告,喔咿第四聲是重擊!(P.68)
一日所遇在此化做一個恐懼炸彈。他的希望是如此微渺,只是想回到台中探視祖母一面,好安切自己的心,然而連如此渺小的願望都破碎,飛機的後補機位輪不到他。
他試著透過一天的對外假期,小心探求一些安穩的因子,沒有多餘的奢想,小心翼翼,求援般地走出戶外,可憐如他,頓時整個世界都與他為敵,他只能焦慮,以及默默承受這一切難堪與冷默的對待。人際疏離的範圍,由此從家庭闊大到整個社會了。每個人對自己以外的周遭事物都顯得陌不關心,層層築起的高牆,訴說著防備與冷漠。總還是天真的認為,世上還是有溫情存在,所謂冷暖人間,有「冷默」也一定會有「溫暖」,但主角的心境本身就偏向有些灰暗,像是伸出了雙手,卻不敢大聲喊道請扶我一把的失意者,安安靜靜的向隅,什麼樣的心境會看到什麼樣的周遭,也許仍有好的事情發生,但在那個當下,已經焦慮到一個臨界點的主角,恐怕只能留意到帶著惡意的冷箭了,他以為他找不到能夠幫助他的回應,每個人給予他的就只有冷默。主角想要全世界之中的一些暖溫,然冷默將他推向了世界的邊緣,候時滅隕。
無論是誰,失意時都希望有人能拉自己一把,或給自己一個微笑,無論是多微小的動作,都能像太陽似的給予溫暖,但試問,如果別人不給予,難道自己就給不起自己一點繼續下去的力量嗎?自己不能當自己一天的太陽嗎?哪怕是一天也好,盲昧期待別人伸援,等同將自己的一切交由別人掌控了。每個人,一定有只屬於自己珍貴的一部分,是別人拿不起也搶不走的,抱持一點陽光心態,也許所遇仍然糟糕,但心境上或許就不會像〈敲門〉一篇,被外界的聲音所影響後情緒紛亂,只知道自己陷入了憤怒的情緒,卻又讓此情緒自殘般焚燒自己了。
第四篇〈暘城〉,講述單親家庭的國小生,面對母親將生活壓力改成對他的誤解、姊姊遠在家鄉,朋友也因家庭背景的衰微排擠他,他書寫家庭完美的假象催眠自己,然累積滿腹的淚水終於無法負荷,而適巧回家的姊姊,給予他微渺希望以期冀未來。
〈暘城〉其實是令人非常難過的一篇。小小的孩子,在面對父親驟逝家庭巨變後,沒有家庭的溫暖給予慰藉了,時逢國小階段,是小孩子初建立友誼與學習人際關係的階段,曾經歃血為盟的朋友,卻相繼背叛了他,一瞬間全部都破裂了,還懞懂無知的小孩,哪裡知曉自己為何會受到這樣的對待。
鄰居長長呼了一口氣,轉過頭不看他說:「你們家很窮啦!我媽說會被帶衰。」
厚重的鐵門關上時發出響亮的一聲卡喳,他只來著及問:「我們不是......」後半句「結拜兄弟嗎?」哽在喉嚨,他說不出來。(P.90)
除此之外,年紀稍長的朋友在面對成長的迷惘時,選擇以強權欺侮來證解,多可怕的惡性循環。拳頭的強勢,其實無法真的得到人心的愛戴,擁有的只有表面稱兄道弟,如果人與人之間的情誼非得以層階建立,對小孩來說,未免是太早接觸的社會現實了。
他們的友情在國中生畢業後就消失了。國中生藉由欺負他來證明自己已經邁入另一個階段,證明自己不再弱小,隔壁巷子裡每個男孩子都是這麼過來的,他不知道這是誰開啟的傳統,現在輪到他來忍受這充滿屈辱的磨練,而改天,過了幾年後,他就會擁有欺負別人的特權。(P.79)
看來有些誇張的情節,其實也只是社會現象的一隅,家長的輿論對成長階段的孩童本身就極具影響力,現在許多社會新聞在播報重大罪行的犯罪者,當畫面播到小孩子時,總是巧妙的打上馬賽克,怕小孩子無論在校園及生活中生存,人們的指指點點,是最殘忍的重傷害。僅管本文中的小孩所遇是父親逝去,家中的債務難以清還,並非任何犯罪行為,但因為有討債公司上門,街坊鄰居就會告誡小孩,誰家誰家的小孩千萬不要靠近,以往被歸類到習以為常的事情,當真的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時候,恐怕只能把無奈與心酸往心裡吞了。
因為採用第一人稱,透過小孩子的視野感受著他每一寸的讓步與每一步努力後的退縮,著實令人心疼。當小孩唸著自己登上國語日報的作品〈甜蜜的家園〉,他自己塑造一個美好的家庭生活,好山好水,家人間互相友愛,是個溫暖而無煩憂的好所在。他一次又一次的唸著,像是要刻盡自己腦袋的唸著。怎麼會淪到這種地步呢?怎麼會讓小孩,無助到要自己創造一個假象,好讓自己有動力持續向前。當假象被道破,赤裸裸的現實襲來,過大的反差,只會更感難受,最後,他試著向外地的姊姊求救了,他再也無法用謊言欺瞞自己一切仍然美好了。姊姊說著一切都會好轉,長大就沒事了,然而,承載所有傷痛的心靈,已無法安穩的長成一個健全的個體,也許現在的一切都會好轉,但未來又會遇到什麼困境呢?沒有人知曉,他也管不著,他連自己的今天過不過得去都不知道,光亮的明天真的會到來嗎?沒有人能肯定,只知道,他自己仍必須走下去。
第五篇〈藍色項圈〉,是在一間象徵權勢財力的私立中學裡,學生們在高壓下激烈競爭,在老師極端不平衡的對待下,學生們一個個在鬧鬼的宿舍寢室裡透過死亡換取新生,貧寒出身的主人公傾盡全力仍無法獲得好的表現,在友人死去的打擊下,他選擇進入鬧鬼的寢室,將自己成為殘酷體制下一員。
只要曾經當過學生,且遇到以成績斷定學校好壞的班級導師,對這一篇肯定是感觸很深。雖是採用第一人稱的我,但主人公從頭至尾都未曾出現其姓名,只是安安靜靜地娓訴他的校園生活,生活的貧困讓他在所謂的貴族學校裡非常不自在,因此他選擇低調,然低調與低落的成績,讓他在校園幾乎抬不起頭來。這裡的老師並沒有扮演傳教、授業、解惑也的角色,他傳達的只有「成績至上」,除了成績,一切都是多餘的,甚至是要求成績好的學生離間成績差的學生,將成績不好的學生視為感染性強烈的病毒,也許是現在教育的方針,使人感覺這部分有些誇張了,許是想要更突出學生在升學體制下的彷徨,加上不能給予救援的老師,使著國中生的主角在此篇中更顯卑微無助了。
乍看篇題〈藍色項圈〉,還懷抱著一種浪漫情懷,當發現這是一種透過上吊死亡卻離奇重生的印記,反倒顯得駭然了。主人公曾經覺得自己特別,因為自己曾在母親的娘胎裡死過一次卻奇蹟似的生還,到了這間學校,他發現他錯了,他在這裡一點也不特別,這裡許許多多的資優生或高材生都死過,而且死過好幾次,那脖頸上的藍色勒痕像是蛇一般的纏成一圈,他們稱之為藍色項圈。我假想,為什麼要求全體都必須住宿的學生宿舍,會有這麼一間全校皆知鬧鬼的寢室,許是多年來許多受體制壓迫下的學生,一個個選擇在此上吊身亡,直到怨氣與執念集合到一個臨界點,便有了神奇的力量。
那間寢室會讓死者再活過來,他們會帶著脖子上的淤青,從衣櫃裡爬回現實世界,然後成績突飛猛進,因為他們已不是人類。(P.115)
以一種鬼魅的方式書寫,也意味著學校對這裡的學子而言,已非學習的殿堂,而是充滿明爭暗鬥,只能在自毀或毀人中做選擇。書中主人公看著學校想著「那是監獄,一棟有著六層樓高圍牆,就算插翅也難飛的監獄。(P.120)」,在許多專家在討論學生們的教改問題時,真的是為學生設想嗎?曾利用大三升大四的暑假,到南投嘉和國小帶一群準備升小二至小六的小學生,當他們的暑期輔導老師,看著他們的暑假作業本,我很訝異,小五的數學題目出現國中才會教的一元二次方程式,題目卻又規定不能設x、y值,因為是數間學校的小朋友集合在一間國小共同上課,大同小異的作業本讓我看到無言,這怎麼會是出給小學生的題目?該是學習基礎的階段,卻一直拋丟越級的知識,怎麼會有辦法消化?簡直要把小學生訓練成萬能妖怪一樣,小孩子的快樂童年呢?我感到疑惑。口頭說著對學生著想,實際上職管教育的人,對國小生的題目自己也不一定答得出來,諷刺極了。對照書中的主角,他便是處在一間要求更嚴謹暴慄的地方,標準是一百分,少一分打一下,當每週假日回家,家人詢問學校生活如何時,可能原想哭訴的,卻因為父親的期待而將所有苦楚吞回自己的肚子,難以消化。
「要用功一點喔!我們可是到處借錢才有辦法勉強讓你進去那裡讀的。」
「嗯,我知道。」
「我們沒有什麼能留給你的,要好好讀書,不要像你老爸一樣,沒有學歷也沒有專長,一輩子讓人瞧不起。」(P.118 -119)
我想,大多同我一樣貧苦家庭中長大的小孩,聽到雙親對自己說這樣的話時,就算在學校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也只會跟書中主人公做同樣的回應吧。所以主人公這麼想的。
幾乎都是這樣的對話,讓我無法告訴他們那個學校的課業壓力早就遠遠超過一個十二歲小男生所能承受的極限,為了生存我們可是幾乎什麼事都幹得出來啊!
挨打到麻痺的掌心,包著深藍色書套咀嚼不爛無法下嚥的課本,裏著深藍色制服的虛弱身體,還有貼著黑眼圈的沉默的臉,而身體與臉的交接處印著一條深藍色的項圈。我的青春期塞滿深藍色的空白。(P.119)
已經不是單純的學習壓力了,如果說學校就是一個小社會,那麼他所面對的,毫無疑問的就是生存壓力,標榜適者生存,不適者亡,殘酷極了!諸多的壓力加上室友阿文的死亡,他終於放棄堅持自己的正道,他選擇了將脖頸套上鬧鬼寢室麻繩,他要成為體制的一員,一起淪落。誰都沒有資格責怪他選擇走上這條路,這是整個教育體系的問題,他只是冰山一角的犧牲品,因為他只是冰山一角,就更令人難過了。國中,本該是充滿叛逆又充滿年少輕狂的年紀,然他的青春期塞滿了深藍色的空白,深藍色,不只是學校制服的顏色,頸項勒痕的顏色,也是他心中滿據的憂鬱,找不到出口的眼淚,凝聚成他悲傷的個體。學習成長,用生命作為代價未免太苛刻,假若連生命都必須要出賣才得以生存,我們的教育真的需要省思,而非將學生當做白老鼠一樣的做實驗,當做在壓模雞蛋糕似的壓出一模一樣性格的學生,覺得失敗就再做一次教改,又是一次全新的實驗,可憐的不是大人,而是在這樣混亂體制下成長的學生。
第六篇〈友達〉,可以說是〈藍色項圈〉的續集,延續著〈藍色項圈〉的發展,為其中阿文的死做解答。警方開始調查阿文的死因,老師直接懷疑成績並非頂端,又曾經是阿文室友,即〈藍色項圈〉的主人公,同樣是以升學壓力為題,不同的是,改以小強做為敘述主體,小強的本名是林友達,「友達」在日文為朋友之意,但他的成績總是吊車尾,所以也是被老師要求學生們排擠的對象,沒有朋友就像是一種諷刺,然他卻像打不死的蟑螂,一路攀升直到優等生的地位,中途也是受到鬧鬼寢室的上吊洗禮,但他非常孤獨,他總想早一步跨入成人的社會,脫離監獄般的學校。他景仰阿文的室友,阿文的室友卻誤以為阿文是他害死的,他原先以為全校除了阿文,也許就只有阿文的室友可以理解他,然一切都是他的假想,他以為,他的世界破碎了,再也沒有什麼值得信任。所以他將所有的情緒封包在一紙信條上,收拾自己的破碎。
紙條懷著小強的訊息在空中一圈圈地翻滾,上面寫著「進入成人世界後,就算被羞辱被暗算,也只能笑給別人看。對方也許臉上帶著微笑,卻可能早就和自己結下了樑子,以為對方是朋友,每次相處都加深對方對我的怨恨,而我,什麼都不知道。」(P.152)
看似強勢的小強,其實跟學校裡的每個人一樣脆弱,甚至他的遭遇跟阿文的室友很相似,都是揹著家人強烈的期望進入學費貴得嚇人的學校,也曾遭排擠,也曾是朋友,其實很雷同的。如果沒有阿文事件的陰影,模糊的畫線在兩人之間,或許能成為莫逆之交也未可知,然誤解在兩人心中紮根,已無其他可能。他做了選擇,他要將一切責究推給阿文的室友,他陷害了阿文的室友。
這是小強懦弱又強勢的反應,因為脆弱所以堅強,因為害怕所以強勢,都只是一種偽裝。誠如〈螳螂〉一篇說的,「人啊,不過是一隻小蟲!」小強不擇手段,讓自己回到班上的核心人物,什麼人情義理全部都拋開了,一切都是假象,他包裝自己的情感,成為體制下的核心,無論精神已被掘空,只剩一具外殼。明明是強勢的踩著別人的背往上爬,卻彷彿能聽到小強泣血般的控訴,是整個局勢讓他不得不如此,一腳踏進了成人世界,也等同捨棄了所有的天真與青春。所以書末說他一腳踏進了成人世界,也等同將自己推向另一處魔境,肉弱強食的現實世界,年輕的身軀裝著如此衰老的心靈,教人怎能不扼腕?
終篇〈伊卡勒斯〉,講述已婚男子矛盾而迷離回憶過去室友忠哥對他的情感包懷,因為他的任性與無以察覺,將忠哥推向了死亡之森的樹海,十年後,搭乘飛機回台灣的過程,他遇見和忠哥極相似的赤松森作,他更改行程的跟隨赤松森作到日本,然他理解他已非過去的自己,忠哥也不復存在了,無法事過境遷,於是他同樣乘著飛機回到台灣,在忠哥給予的回憶中反覆傷害自己。
〈伊卡勒斯〉以過去跟現實雙線並行,過去的自己恣意忽視忠哥的付出,就算是想回以溫暖的語句,說出口的卻總是傷人,忠哥看似默默的承擔,心中卻藏著一把野火,將自己一點一滴的燃噬,並以南方之星的〈真夏的果實〉貫穿全場,歌詞明白的表示:
「正如負一百度的太陽,談一場不會帶來溫暖的戀愛。令人眩目的真夏的果實,至今仍綻放心底。」
原來是一場絕望的戀愛。(P.163 - 164)
年輕時戀愛的界限模糊不明,透過一曲絕望的歌曲,暗渡了忠哥的心情,儘管多年後,主角了解也深受憾動,卻也改變不了天人永隔的距離,如此相近,又難以靠近了。
十年前忠哥走進樹海,現在的我躺在赤松森作身旁。時間與空間現在都是模糊的線條,可以任意扭曲或折疊,我背負著十年的寂寞往回走到原點,而忠哥卻在十年前就停下來等我,一直等到我能愛他為止。(P.183)
同志之情被視為違反常理,所以作者選擇用死亡的距離讓他們彼此貼近,一把野火將彼此焚燒,差別在於,前者忠哥走近樹海,後者的自己則被忠哥判了終生監禁,獨嚐往後一個人的孤寂,然他不能再想了,他有妻兒等他回去,他已經不是像年輕時可以對忠哥耍任性的自的,忠哥曾受愛火燒疼的苦,他用回憶反噬。再不能回去了。同性戀在台灣已起步,近年來諸多的活動舉辦,如同志彩虹遊行,在台灣已經成為同志每年的例行活動,他們是少數的一群,但並非病態,也非活該受歧視。總有一天,他們也能走向自己的路,而非像〈伊卡勒斯〉裡的三個男人,徘徊在社會的邊緣,猶豫要不要跨過最後一道性別的防線,還是受制於現實社會的倫常壓力。
再者,〈伊卡勒斯〉放在最後一篇,也有統整七篇之意,神話中的伊卡勒斯與父親用蠟造了一對翅膀一同飛離宮殿,然伊卡勒斯忘卻父親的警告,愈飛愈高,直至蠟融的翅膀,伊卡勒斯從高空中狠狠摔落。
每一篇的人物都在面對生命成長各時期的困頓,張耀升在介紹《縫》的時候做了如此解釋:
五年級的《伊卡勒斯》、《縫》,六年級的《螳螂》、《敲門》,七年級的《藍色項圈》、《友達》、八年級的《暘城》,是這個世界上五年級以下的所有人同時承受的創痛,也是他們曾經、目前、或將來得面對的難題。
每個人都耗盡心力的面對挫折,往自己心中美好的夢想前進,同時也因為追逐夢想而燒融了羽翼,〈伊卡勒斯〉裡強調「飛機起飛還是為了降落」,以此為每個人的墜落下了注解,明明都是如此的拚命,為微小卻重要的夢想而努力,卻總在起飛與降落中飄盪不定,就算克服了現下的困難,未來仍然得面對數不清的難題,愈是努力,愈是容易產生裂縫,就如同伊卡勒斯,飛的愈高,高到靠近了天,代價是愈深的陷落。萬劫不復的像是詛咒。
綜觀此書,張耀升沒有選擇帶有希望結尾的方式,呈現了成長時期的黑暗面,投射一團又一團的負面訊息,集結成一個偌大的黑洞,教人震懾書中篇幅的同時,也受到巨大的陰暗氣息影響,換個方向來看,也帶著一種期許,狄更斯《雙城記》在卷頭便寫道: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面前有著各樣事物,人們面前一無所有;我們全都會上天堂,也全都會下地獄。
當所有負面凝聚到一個臨界面,全新的力量也將誕生,許是中國人說的否極泰來了,正因為有黑暗的經歷,才更能體會與珍惜感受光明與希望的瞬間。且成長,是一條不能回頭的路,只能選擇繼續前進,或原地踏步後被時間催著年華老去,就算努力所換來的是持續不斷的墜落,也是一種成長,一路上所有的苦痛辛酸,也許年老時回想,一切苦難都已是微風吹拂而過一片落葉,輕描淡寫了。
---------。。
後記:
破了自己寫心得的字數紀錄啦!果然,有老師逼著分析小說做報告就是不一樣啊!
但......唔,正常的小說心得,是不能這樣把內容爆光光吧,但這是小說賞析兼心得報告,所以,啊哈哈......因為小說老師大好人的給了很好看的報告分數,所以很高興的放上來啦文章標籤
全站熱搜